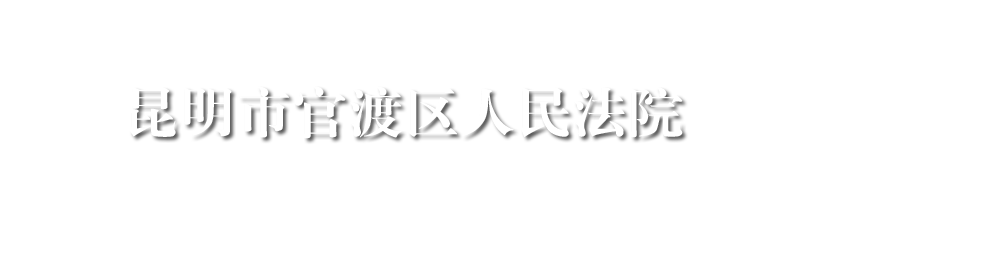[本案提示]
这是一件因公安机关未及时履行查处案件的法定职责而引发的行政不作为纠纷案件。受害人丁阳春受到他人不法侵害(涉嫌强奸)时,是一个尚不满四周岁的小女孩,面对如此脆弱的生命遭受如此残酷的伤害,作为国家赋予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不是及时、迅速地履行查处案件的法定职责,而采取的是漠不关心、消极拖沓的工作作风,贻误了收集犯罪证据的最佳时机,致使犯罪嫌疑人终因证据不足而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案件发人深思。
[案情]
原告(上诉人):丁阳春。
法定代理人:杨丽芳,原告之母。
委托代理人:冯烈华,小板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
2004年2月29日下午,原告丁阳春之母杨丽芳为其洗澡时发现其外阴部有血迹和新鲜裂口,追问其原因,丁阳春称上午到邻居张某某(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名为张兴荣,男,汉族,1952年6月16日生,重庆市人,住官渡区六甲乡陈家营村96号)家找小朋友玩时,被张兴荣强奸。原告丁阳春的母亲杨丽芳遂将此事告知了朋友张健,后张健于当天下午17时许向被告所属六甲派出所报了案。接到报案后,六甲派出所先后派了三名联防人员及一名干警随同张健前往原告家,将原告带至云南妇产科医院诊断,之后返回派出所,当天未到案发现场。2004年3月1日中午12时许,被告所属六甲派出所派对张兴荣进行留置盘问,并对其住处进行现场勘查,3月3日以张兴荣涉嫌犯强奸罪对其予以刑事拘留,3月9日向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批准逮捕,3月17日官渡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3月18日被告向张兴荣送达了《取保候审决定书》。原告丁阳春的伤情,根据昆明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左阴唇沟有一约0.8 × 0.1× 0.08的新鲜裂口,经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人体损伤法医鉴定中心鉴定,已构成轻微伤。案发后,原告以被告接到报案后未及时对犯罪现场进行勘查,未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及讯问,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破坏现场及与他人订立供守同盟的机会和可能,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后期调查工作,导致目前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得不到法律的追究,自已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被告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30万元。
庭审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传唤了证人张健到庭,其证实:事发当天被告的联防人员及民警均未到过案发现场。被告对此证言无异议。
被告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以接到原告的报案后即带原告去检查、验伤,于次日对现场进行了现场勘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留置盘问及刑事拘留,已经完全履行了应尽的职责为由进行辩解,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审判]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经一审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在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被告在接到原告方的报案后,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是:立即查处案件。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表明,被告于2004年2月29日17时许接到原告方的报案后,并未到过原告报案称的现场,直至次日,即3月1日12时许才对涉案嫌疑人进行留置盘问,对其住处进行现场勘查。此时距原告报案时间已超过18个小时之久。 故被告在接到原告报案后没有履行立即查处案件的法定职责,其行为已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但原告关于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目前尚无明确赔偿的法律依据,赔偿应以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原则。故对原告的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二、驳回原告丁阳春要求被告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赔偿其精神损失费人民币300000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丁阳春不服原判决,提出上诉称: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前提下,其主张的精神抚慰金理应得到赔偿。
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坚持一审中的诉讼主张,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丁阳春撤回了上诉。
[评析]
合议庭在评议时,归纳了本案的两个焦点问题:一、被告的行为是否已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二、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有无法律依据?并着重地围绕案件的这两个焦点展开了讨论。
关于焦点一:被告的行为是否已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合议庭成员意见统一,一致认同被告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首先,从概念入手,对行政不作为违法做了定义阐述: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或依行政行为相对方的申请,应当主动实施行政行为,而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漠不关心、不当延误或是在依申请行政行为的场合,行政主体对相对方的申请不予答复。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两种不作为的情形:1、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应当履行行政行为而完全未履行,或者行政机关依行政行为相对人的申请,应当答复而未予答复。2、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漠不关心、不当延误。在第1类情形之下,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在定性时较为容易,较为直观。第2类情形之下,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就有较大难度,因为在此类情形中,法律、法规通常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履行义务的具体期限,而形式上又往往表现为行政机关也履行了一定职责。本案正属第2类情形:被告在接到原告的报案后,派人带原告到医院进行了检查,于次日对案件采取了现场勘查等措施,这些事实成为其主张不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抗辩理由。故如何把握“不当”的度,就是解决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所在。接着,从法律、法规入手,紧扣条文的立法宗旨,从条文中明确了本案中被告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在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第一条规定:“现场勘查是侦破刑事案件的首要环节。”第二条规定:“教育基层公安保卫人员和治安保卫委员会的人员,获悉发生案件后,应立即组织力量保护现场,…发现犯罪分子尚未逃离现场时,应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上述法律、法规均多次用了“立即”一词,据此确定被告的职责为:在接到原告的报案后应当立即查处案件。尽管从条文看,确实没有明确被告作为的具体时间,但可以看出,法律、法规对被告履行查处案件的职责有相当严格的时间要求。评议时把重点放在了对“立即”一词的理解上,“立即”一词虽是时间上一个泛指概念,但根据《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立即”一词与“立刻”同义,义为“紧接着某个时间”,具体到本案,被告履行“立即查处案件”职责的时间,应当理解为接到报案后即行开始。而审理查明的事实是,被告接到报案后,并未立即对案件进行查处,直至次日中午12时许才对犯罪嫌疑人留置盘问,对其住所进行现场勘查,此时距原告报案时间已超过了18小时之久,其行为完全符合“不当延误”的行政不作为情形,超出了“不当”的度,故根据上述理解和分析,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作为违法。
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有无法律依据?合议庭评议时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行政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尚无明文规定,故原告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第二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本案中被告的作为已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是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且本案中原告丁阳春受害时尚不满四周岁,刑事案件未能侦破,犯罪嫌疑人未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与被告不当延误的不作为违法行为有直接关系,此案件在当地造成了不良的社会负面影响,给原告及其家人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是不言而喻的。故认为应当由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合议庭评议时,结合本案事实,通过对有关法理、法律法规的分析,持慎重态度,倾向于第一种意见。主要理由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责任问题的批复》是答复四川省高院的一份批复,系个案指导意见,并不具有法律适用的普遍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尽管原告的此项主张符合情理,但现行国家赔偿法中关于行政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尚无明确规定,于法无据,故不应得到支持。
从上述两个焦点问题的分析及处理结果看,似乎存在一个矛盾,就是被告的行为既然被认定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为何又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这也正是笔者提出来与大家商榷的问题。因为任何违法者对其违法行为都应承担法律责任,这是“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基本要求,被告能否例外?在该案中,关于行政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律明文规定,能否成为被告免责的依据?原告的合法权益将以何种方式得到救济?无疑,违法者未能得到法律的追究是一审中存在的一件憾事,但值得一提的是,据悉,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丁阳春撤回上诉的真实原因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庭外达成调解协议,被上诉人自愿赔偿给上诉人丁阳春精神损害赔偿费40000元人民币。至此,本案可谓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果,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在法制化进程中,如何促进和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法律如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体现“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关于行政精神损害赔偿能否成为有法可依的现实等等。相信随着法制化进程的完善,这些问题在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个合理的答案。
一审判决书:官渡区人民法院(2004)官行初字第10号
二审裁定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昆行终字第97号
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
审判长:冷雨静; 代理审判员:罗诚 龚钰 书记员:文若钰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